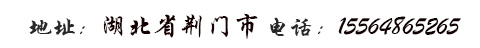绿森林葵花杯大赛,参赛文章6号一10号
|
绿森林.葵花杯"父亲,我想对您说"征文大赛如火如荼进行中,参赛作品雪片般飞至绿森林;作者们可谓大展文笔,文采飞扬。演绎出一篇篇感人肺腑的父爱神话..... 敬请尚未投稿的花粉们赶紧投稿! 大赛初衷:忙碌的父亲节刚刚结束,承浴着父爱的阳光,在这个太阳花盛开的六月,绿森林大型亲情征文活动含花带雨漂涌而来,愿此次活动的种子,在阳光能照到的我们大招远的每一寸领土,亲情花开……漫山满野…… 拿起手中的笔,用真情写下那些藏在心底的对父亲要说的最诚挚的语言!《父亲,我想对你说》征文大赛,面向社会征稿,体裁不限,题目自拟,字数字以上,约稿者从学生到学者,从家庭妇女到社会精英,从村夫到高官,从小职员到大老板……只要有爱您就来,欢迎围观欢迎投稿,收稿截止到6月30号。关于文章涉及内容,只要是讲述和父亲的故事,父亲的生平,或父亲和母亲……这类反映亲情情感方向的文章都可以写都在征稿范围。 这次活动的奖项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作品奖 所有参赛作品由五名资深专业人士组成的评比团队对作品进行打分评选。 一等奖一名绿森林现金卡元 二等奖两名绿森林现金卡元/人 三等奖五名绿森林现金卡元/人 第二类:网络投票人气奖 7月1日开始在绿森林公众平台对征文进行网络人气投票。从现在开始,根据投稿的先后顺序开始在平台上陆续投放参赛者文章,敬请广大读者尽早阅读,选好自己喜欢的文章,以备7月1号开始投票,投票时间一共三天,根据得票数量直接设定奖项如下: 人气第一名,奖绿森林现金卡元。 人气第二名,奖绿森林现金卡元。 人气第三名,奖绿森林现金卡元。 人气第四名,奖绿森林现金卡元。 人气第五名,奖绿森林现金卡元。 人气第六名,奖绿森林现金卡元。 人气第七名,奖绿森林现金卡元。 人气第八名,奖绿森林现金卡元。 所有投稿者均可获得父亲节推出的99元向日葵瓶花作品一个和60元的一次性现金抵用券一张,凭身份证和稿件出示到绿森林鲜花店自取,领取时间7月1号到7日30号。 6号作品 父亲,我想对您说 作者:梧桐细雨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 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 等我长大后,山里孩子往外走 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 盼儿归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 都说养儿为防老, 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 都说养儿为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 儿只有清歌一曲和泪唱,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 父亲,我想对您说,想起您,总会唱起这首歌,多少年过去了,曲已老去,纯朴的清词,浅吟至今,翻滚的心潮,从未退去,每每,父亲节,您的生日,想起,然后,缓缓唱起。 上中学的时候,写了篇作文《父亲的手》,老师让我当成范文在讲台上给同学们念,念着念着,自己竟流下了无声的泪水,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那是一篇朴实无华的学生作文,却是一个十六岁女儿全部的爱与心疼。 拂去日历上的尘埃,日子醒目,今年,是您人生的第八十五岁生日,树叶正绿,稻浪似火,您的人生却悄然进入冬季,脸庞上难填的沟壑,微驼的背,疼痛的关节...给您买衣服,突然记不起您的腰围,想来,有多久,没亲手为您换上新装了?我只能用这样简单,直接,自私的方式,去表达我所谓的孝行,而您,需要一方天空,就像我们小时候,您为我们遮风避雨那样的天空,而我,只是默默望着您,望着您被半生风雨打湿的沧桑,惆怅,却无力。 一些记忆里的片段,您是一位老党员,常常给我讲起您40,30,20甚或更远的年华,饥饿,困顿,屈辱,清寒,我一面在那些没有光亮的日月里打捞光与影,一面对您对命运的不屈与平和之心深深感恩,我经常托着腮,静静听着,然后多想,走上前去,给您一个深深的拥抱,一边伤痛着您渐然老迈的身躯,一边又极力,想多留些这光亮岁月里的温暖给您…… 物质及其匮乏的年代,您是喜欢喝酒的,量可以,每天中、晚餐都会小酌两杯,无论如何清贫,母亲都会把下酒菜弄的香气四溢,有时是自家菜地里的清新小菜,有时是来自市场的一条带鱼,更多时候只是一叠红艳艳的花生米,我常常看到温酒的小炉子上冒着滋滋的热气,您一边小口品咂,一边与母亲及儿女们聊着家常,暖极了,我会在那一刻,看到您脸上满足而舒心的笑,我会觉得,酒香,是这世上最好闻的香气,我还在心里发誓:等我长大了,挣钱了,我一定会给父亲您买最贵最好喝的酒。 一转眼,好多年,您一直延续着这个嗜好,子女们亦争相为您购买各种酒。如今,储藏间里总会有些色彩丰富的酒盒子,酒瓶子,算不上价值不菲,比起您的年代,已算是奢侈的了。您由于手术遵医嘱戒了酒,得闲回家午餐,我在收拾物什的时候,看着那些酒出神,想起,若,您还能喝酒,我一定,在冬天的炉火里,亲手为您温上一壶,然后,陪您浅酌,微醺... 等待生日时再为您订个大大的蛋糕,只写上6个字:安康,福寿,连年! 7号作品 《父亲的事业》 作者:玉蔷薇 我上次回家的时候,问了父亲关于广播事业早期地一些事情,我说我想写一篇《父亲的事业》,我明显地感觉到父亲的兴奋以及他隐隐地期盼。 可是,回来后心情一直都是糟乱的,每欲提笔,又感自己能力低微,无法描述父亲平凡而又辉煌的事业成就,完成不了一篇父亲所期待的文章。我也只能捕捉记忆中与父亲的事业有关的一些情节,记叙下来,也并不奢望能博父亲一悦了。 我还记得我小学里的一篇作文这样写道:“我走在去姥姥家的路上,寒风凛冽,雪花飞扬,冬天的田野因荒芜而空旷。这时,我看见了父亲,他们一行几人,抬着电线杆行走在空旷的田野上......”我的这篇作文得到过老师的赞扬,所以记忆犹新。 后来,我问过父亲,那漫山遍野的电线杆,难道都是你们一根一根树立起来的吗? 父亲说:“是的。最初用的是木头杆,三五年之后就腐烂了。后来又用了一百根石条杆,石条杆不腐烂,但是弊端是矮,只有四米,有碍交通。后来,我创办了一个水泥杆厂,水泥杆的高度是六米三,,又不会腐烂,最后就全把木头杆换成了水泥杆。” “啊?你还办过一个水泥杆厂?那么那个厂子呢?”我好奇地问。 “以后就转包给别人了,条件只是每年给广播站无偿提供根电线杆。”父亲答。 时光似乎一下子穿越回到了年,20岁的父亲来到了广播站,站上只有一台手摇发电机。我似乎看见年轻的父亲拼尽全力摇动起一台发电机的情景,而那时,全镇没有一个村是通了广播的,也可以理解为,空旷的田野里没有一根电线杆......我现在仍然惊叹,父亲他们,是怎么在全镇这么广阔的田野山间架起了一根一根的电线杆,最终使村村通上了广播,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一些文娱的信息最终送进了千家万户。 待我记事的时候,家里的墙上就已经挂着一个长方形的盒子,里面应该是一只喇叭,它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准点地响起,也会准点地结束。后来,我的年近90的姥姥说话时居然用了一些诸如“牺牲”“奋斗”等时髦的词语,我们问她哪里来的?她说:“广播里听来的。”是的,那时的广播犹如在我们混沌的世界里打开了一扇五彩斑斓的窗户,每天的新闻、歌曲、评书,曾给多少人带来希望和愉悦。要是谁家的喇叭坏了,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会马上找到村里的线络员去修理。那时的初秋经常会下很大的雨,一下就是几天,田间的电线杆经常会被大风刮倒,有时也会出现整个村线络不通的情况。这时候父亲就会背上铁鞋,带领三两个人的维修小分队,跋山涉水,奔赴田野山间那些倒伏的电线杆。 我去过父亲的机房,那里的一台设备上闪烁着各种颜色的光,那大概是一个传输器,所有的信息,通过它传输给千家万户。有时候,父亲会做一个禁止我出声的手势,然后按下一个按钮,对准话筒说:“下面广播通知......通知:经研究定于本月X号,也就是明天,在公社党委会议室,召开全公社各大队支部书记会议,时间一天,自带午饭,望各大队支部书记准时参加,不得有误。XX公社党委办公室。X年X月X日。” 我对父亲说:“你们做的这些属于公益事业,应该是有财政拨款的吧?” 父亲说:“可能上面是拨款了,但是镇上财政是一分钱也不曾给过的。” “那你们那些维修费以及各村线络员的工资支出,钱是从哪里来的?” 父亲说:“靠的是家家户户的集资。以前是每户几毛钱,后来是每户每年一块钱。” 是的,我记得在广播里听到过父亲做的关于集资缴款的动员报告。他说:“每天早晨的5点25分,你家的广播会准点响起,比你家的闹钟都要准时。你家喂只大公鸡早晨打鸣,你不得每天喂它把棒米么?这一年下来也不止一块钱吧......”那叫一个情真意切呀。好在那时民风淳朴,所以集资还是比较顺利的事情。 父亲在他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三十几年,他见证了家庭广播这件事物从无到有再到消失的整个发展过程,他退休的时候,家家正在安装闭路电视。应该说,他的一生为文化传播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查阅“事业”一词,它的解释是:事业是指人们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的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 我们姊妹几个后来所从事的不过是一种职业,或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都不能算作是事业。我觉得唯有父亲所做的,才可以被骄傲地称作是“事业”。 父亲渐渐老了,那些家家户户的喇叭也早已被淘汰掉了,可是,漫山遍野,那些电线杆应该还在吧?我多么希望还能看见父亲,穿着那种带弯钩的铁鞋,爬上高高的电线杆,还能看见他抬着电线杆,行走在田野山涧...... 8号作品 为父为子 作者:林晨 我自认为是一个敏感而木讷的人,敏感在于我总能敏锐的捕捉到感情反应,木讷是在于我几乎从不表露自己的感情。比如前些天的父亲节,那天我甚至都没有见到我的父亲,也没有任何的节日表现。 我与我父亲的关系,如同大多数普通独生子家庭的父子关系一样,年幼时崇拜,青年时反叛。在我最早对电视产生记忆的时候,成龙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明星,而在我童年时,我的父亲很像成龙,长发、健壮、个子不高、国字脸、大鼻子。跟很多父亲一样,他从小不太管我,教育是母亲的事情,他觉得男孩子要玩,要爱干净,要有教养,其余的事情就全都交付我的母亲来管束我。当时觉得我父亲真够朋友! 十八岁之后我离家外出读书,在我二十岁那年的父亲节那天,看到了《人物》杂志的一篇文章,标题就让我我印象深刻:“失去了在一起的时光,才会明白如何为父为子。”我从那一天开始思考我的父子关系。 今年我二十二岁,在南方工作一年后回到家,回到我十八岁之前家族就给我安排好的人生里面,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以及跟家族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 我对目前的生活不满意,比我回家之前想象的还不满意。我不相信我的一生会在那么多年前就被决定,决定的甚至有点草率,在我奶奶的病床前面。我依稀记得我的父亲几乎没怎么参与讨论,他同我一样,接受了长辈讨论的结果:随我大爷读工科,回来走我大爷的老路。在我所生活的小县城,这是一条很不错的路。那时我不懂,我只懂听长辈的话。现在看来,很像宿命。 情绪的变化也是从我回家之后开始的。我曾经是一个很有办法的年轻人,像所有在外漂泊的年轻人一样,年轻富有朝气,做事情干脆利落,过着自己的生活,暂时摆脱家族的引力影响。我不知道一个年轻人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否是明智的,但是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做了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互相模仿,而是我们就要这么选择。回到家里后,一切都变了,我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国企工作,每天朝九晚五,工作内容枯燥单调,非常轻松。傍晚下班,吃过饭也没有任何活动,每天就跟几个老同学出去喝喝酒。我开始变得懒惰,变得没有动力,变得丧。 我失去了在外漂泊的三年里那种年轻人的特质,我不再学习新的知识,不再接触新的事物,甚至都很少交新的朋友。刚回到家的几个月里我甚至开始抑郁以及自闭,间歇性的崩溃躁郁。原本话痨的我开始寡言;每次与家人朋友吃完饭回家之后都会觉得很累;每次笑过之后都会给自己一个哭脸;从来不在食堂与同事一同吃饭;开始回避所有能回避的社交场合;只跟几个朋友每天在外面喝酒。 我父亲的放任在这个时候,终于开始变成了不作为的烂招数。家族中的其他长辈开始指责我的父亲对我没有管教,我也开始觉得父亲没有了立场,对我的遭遇袖手旁观。而我,几乎失去了对我生活的控制,真正成为了一个自己生活的“局外人”。 家族对于孩子的控制应该是许许多多的同龄人遭遇过的,我看过很多相关的文章电影,特别是曹保平导演的新片《狗十三》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解读。电影上映后我写了一段话: “家长的照顾有时候难以消化到令人窒息,在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家长在照顾孩子,而是孩子在受到家长照顾的时候,反过来照顾家长的感受。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我们想要自己做主,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我重新思考了我与父亲的关系之后,我发现我与父亲的关系的恶化本质上不是我对父亲这个具体角色的厌恶,而是我对我们家族——一个典型的传统父权家族——的反抗。我的父亲被我跟我的家族夹在中间,他既要照顾自己儿子的感受,又要兼顾家族安排给我的宿命——虽然他一个也兼顾不到。父亲就成了抽象的家族观念的具体形象,成为了我反抗家族宿命的具体目标,甚至成为了我发泄心中不满的那个假定对象。 父亲做错了什么呢,他其实什么都没做,从小对我就是放养教育,没有参与我的重大决定,没有参与关于我未来的讨论,也没有扼杀过我的爱好与梦想。他真的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从来不像网上所描绘的父亲的伟岸与伟大,他就是一个普通县城里的一个普通父亲。二十三年来他没有刻意的改变他的教育方式,没有刻意的束缚我的脚步,也没有刻意娇惯我的坏毛病。但是当年轻一代与传统一代在生活方式上产生了冲突之后,慢慢老去的他也只能站在我的对立面,成为我反抗的对象。 曾经我与父亲“失去在一起的时光”,我以为能够“懂得如何为父为子”,但是重新回归到家族,我发现我对“为父为子”的理解远远不够。同样的,我回归家族之后,我与家族的意识形态的矛盾,可能比“如何为父为子”更加棘手。 所幸我至今没有与我的父亲交恶,也没停止对于自己的生活的向往与争取。我还会继续走下去,直到与父亲和解,直到与家族和解。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 9号作品 回忆我的父亲 作者:李绥花 我的父亲因为胃癌去世已经八年了,总会在不经意间回忆起父亲,音容笑貌依然是那样的清晰,未曾忘记。 父亲是一个小心谨慎,开朗大方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少有文化的老人。父亲年轻时一直在村里当个小村官,职位不大,但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的雨季,要是遇上连雨天,那时通讯差,爸爸总是先爬到村子中央用树木架高的三角台子上,用力的打铃,然后下来敲着锣,围着村转上几圈,边敲锣边吆喝,意思是让村民做好防汛工作,那时觉得是好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父亲的大爱之心。父亲做人做事谨慎小心,记得刚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村里因为效益好,村委成员年底每人发元奖金,爸爸真真切切的没拿那份本该属于他的钱,父亲认为那便是贪污,占国家便宜,这便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最底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现在说来,让人笑话。父亲性格开朗,走到哪,那就有笑声,脑子特好使,几乎算是过目不忘,每次镇上开会,我们村都是我爸去,而且从不记笔记,回来转达就能做到一流淌水背出来,从没出过差错。父亲人缘好,一辈子没跟村里人吵过架,对我们姊妹三个更是关爱有加,做事光明磊落,不占别人便宜,是父亲一生的写照。如今父亲走了,带着深深的眷恋与不舍离开了人间,我知道,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却又觉得是那样的无奈与心痛。 爸爸,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记住您的教诲,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与人为善,无愧于心。 10号作品 祖母的修行作者:石爱云老屋灶台前,祖母盘腿坐在蒲团上。一缕暖阳穿过虚掩的黑色半门,落在她一侧身上,照亮了半边脸。 她的腿上,一条黑色抿裆裤,扎着同色绑腿带。软底绒面浅口鞋,露出一截白色线袜,紧紧绑在腿带里。灰蓝搭襟盘扣夹袄,浆洗的板板整整,没有一点褶皱。头发虽稀薄却少有几根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在脑后绾成不大的髻,用黑色发网蒙罩起来,清爽利落。 那个蒲团,棕绳盘编的,坐了几十年,边沿有些破损,用深蓝印花麻布包缝了一圈儿,倒显得别样雅致。蒲团中间已经凹陷下去,表面也看不到棕绳原本硬铮铮的毛刺,反倒有一层经过漫长岁月才能慢慢磨就的光亮,摸上去,滑溜溜的。 祖母一手拉着风箱拉杆,一手往灶膛里填着柴草。两根风箱木拉杆,磨损得很细了,像两条走着缓慢舞步的瘦弱的腿,在祖母手臂的带动下,前走着后退着,随祖母微微前倾继而稍稍后仰的身体,不断重复着流畅却又单调的韵律。 老旧的风箱在海草顶的老屋里,“呼—嘎—呼—嘎”,沉闷地吟唱,仿佛来自遥远地方的古老民歌,或是佛歌经咒。 古稀之年的祖母,如打坐般笔挺着身子,只在查看灶膛里的火时,才偶尔弯一回腰低一下头。 祖母盘腿,不是两腿叉在一起,膝盖悬空那种,是把两条腿柔软地交叠一起,紧贴蒲团,与地面平行,同时腰板儿挺得笔直,头昂起,如同那些专业舞者的姿态。 她以这种近乎修行的坐姿,每天三次,在灶台前坐了几十年,直到八十多岁,像笃信某种宗教的教徒,虔诚地面对自己一生追随的信仰。 不知道她头一回坐到灶台前,是否也是这种坐姿?那时她应该是个新嫁娘吧?未出阁时,她的娘家是岛上有钱的大户,住着青砖灰瓦的大房子(解放后县政府办公场所,又称西大院),她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小姐,厨房的门都没有进过。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祖父意外去世,三十出头儿的祖母,拖儿带女,离开城市,回到海岛,独自肩负抚养老人养育孩子重任的时候,灶膛前的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她常和跟着她长大的我说,人活着,就要活出个精气神儿,要昂起头挺直腰板儿,越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遇到迈不过的坎儿,越是要这样! 困难时期,有男人的人家日子都不好过,孤儿寡母就更难了。祖母是个很少掉泪的人,她说一辈子的眼泪都掉在那会儿了。 那时候,岛上家家堂屋都挂个干粮筐。从屋子大梁上垂下一条一米左右的绳子,末端拴个木头挂钩,吊着一个柳条筐,专门放干粮的。悬空的干粮筐对着北面后窗(岛上叫后门),空气通透,干粮不容易变馊。 家里两个老人,一个是祖母的婆婆,另一个是她收留的无儿无女的远房亲戚。俩老人也愁这难过的日子,动不动偷偷翻看一下干粮筐里还剩多少干粮。饥饿的孩子们一天好几回踩着凳子到干粮筐里找吃的。看着食不果腹的一家老小七口人,再看眼空荡荡轻飘飘的干粮筐,祖母躲到没人处偷偷抹眼泪。 不管多难,日子还得过。曾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祖母,忍着饥饿,拐个大篓子,迈着当年家里怕她遭罪、裹了一半儿没有裹成小脚的半大脚,出去翻山越岭挖野菜。苦菜、婆婆丁、管豆花、银青菜、山苜楂、灰菜、碱蓬菜……只要是没有毒的,连个菜根儿也不放过。冬天,山上没有野菜了,她就忍着刺骨严寒,踩进冰冷的海水,捞各种可以吃的海菜。 她自嘲,没裹小脚,是老天爷早就安排好的,这双半大脚就是为了上山下海准备的吧。 她丢下当年矜持大小姐的脸面,走街串巷,低眉垂眼去乡邻家讨借一把玉米,一瓢麦麸……往家回的路上,脸上都是泪。 祖母是个吃穿都很讲究的人,即使生活贫困到了那种地步,她还是要变着法子把日子过出滋味儿来。她把各种来之不易的食材做出多种花样,每天的饭菜叫它不重样儿,让家人对每一个并不明朗的明天都不畏惧,有个小小的看似不经意的期待。孩子们的衣服破了,破洞上她给织出一朵朵素淡的小花儿,欣欣然地开着,让孩子感觉,再难的岁月一样有美丽盛开。 灶膛前,她端坐得如同一朵莲,和饥饿的孩子一起,虔诚地盯着从锅沿儿冒出的一缕缕飘着淡淡饭香的蒸汽。欣慰地看着蒸汽一圈一圈飘逸到清冷的空气里,温暖着一家老小渴望的眼睛。 孩子们跑到灶台前,围着她,依着她,靠着她。他们心目中,母亲笔挺的身体就是一堵坚挺的墙,有了她,他们什么都不怕。母亲给他们遮寒的衣裳,给他们暖和和的一铺炕,她还能稳稳地盘坐在蒲团上,“呼—嘎—呼—嘎”,让风箱唱着歌,变戏法一样,从锅里冒出天下最香甜的饭香味儿…… 祖母娘家是“高成分”,她二叔又是解放前岛上的设置局长,岛上级别最高的行政官员,从东北拖儿带女回来时还是跟着二叔坐着国民党军舰回来的,祖母成了村里的重点批斗对象。 村里场院批斗场上,祖母站在台子中间,浑身上下拾掇得利利索索,头上还特意抹了从东北带回来的又香又亮的桂花油。她面色平静得似一潭秋水,抬着头平视着前方,身板儿挺得比平时还要直。她看起来不像要被批斗,倒像戏台上的一个女主角。 祖母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地说,如果说俺二叔是坏人,你们把他从台湾抓回来,俺也出来批斗他!俺半辈子行的端走的直,谁也没怕过!在东北那会儿,日本人我都没怕,俺还会怕咱乡里乡亲的?如果就是不想让俺活了,也行,谁逼俺,就把一家老小给他养着!没有替俺养的,俺就回去做饭了! 几句话说完,祖母就在一片无可奈何的目光里,回转身,挺胸昂头大步流星回家了。一进门,就盘腿坐到蒲团上,“呼—嘎—呼—嘎”做起饭来。 风箱发出的闷响,叹息般,一声一声,安慰着她。她大把大把往灶膛里填柴草,所有的委屈愤怒,被她使劲儿丢进灶膛里燃烧的通红的火里,风箱拉得越来越响,火越烧越旺……家里老人孩子还在说说笑笑,谁都不知道外面场院上发生过什么…… 儿女长大了,成家了,艰难的日子也都过去了。所有人的日子都过得越来越好,做饭有了煤气灶,鼓风机也替代了木风箱。 要强的祖母不用儿女管饭,坚持要自己做,依然一口大铁锅、一个老风箱、一个大蒲团。 我打三岁跟祖母过,直到出嫁。多少年习惯了,每天放了学下了班,走进家门,拐过照壁,就看到了灶台前蒲团上一字一板拉着风箱的祖母,腰板儿永远挺得溜直,穿戴总是干净整齐。 蒲团上,她或是沐在正午的阳光里,或是身披西沉下去的斜阳。那些温暖的剪影,竟充满了令人心生感动的仪式感,我的心每每都被那些时刻温柔地触动着。 祖母拒绝燃气灶、鼓风机这些省时省力的新式玩意儿,她说,老物件、老章法做的饭才香,才好吃。我们都笑她观念陈旧思想落后,说她说的没有道理。她也不争辩,就一句:一辈子,习惯了,就这种过法了。然后,我行我素。 直到这几年,她走了快二十年了,在大家开始崇尚返璞归真、寻找原生态生活的时候,才明白,祖母当年没说错:老物件、老章法做的饭才香,才好吃。 前阵儿,去一家农家乐吃饭。农家大嫂穿了一件搭襟盘扣袄,拉着风箱用大铁锅在做饭。顿时觉得好亲切,想起了祖母。 再看,大嫂坐在一个板凳上,凳子高,她在撅着屁股低头弓腰烧火,锅底不好烧,呼呼往外返烟,她揪着脖子上的围巾捂着脸,咳嗽着,拉的风箱也像跟着在咳嗽,“呼嘎,呼嘎”,上气不接下气。 有些失望,继而又想,现在又有几人能如祖母般,在灶台前坐成一朵莲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anggoudasai.com/wgdszl/3856.html
- 上一篇文章: 年,欠钱不还者要完了国家出台1
- 下一篇文章: 花儿少年深圳首届儿童模特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