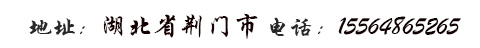台湾心理治疗总舵主解读一文讲透两岸心理发
|
本文字稿整理自王浩威老师主讲公开课:“一个台湾咨询师眼中的大陆心理咨询和治疗”。 01 在台湾,很多心理治疗界特别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心理工作者,几乎都有一种隐士倾向:他们扎实地做自己的学问、好好读书思考、在自己的诊疗室里跟来访者相处、被分析等,大部分都对来大陆讲课不太感兴趣。台湾的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学习过程跟大陆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部分精神病患者被相当不人道地收容——用笼子关着、铁铐铐着。那时,精神科医生的主要工作是照顾慢性精神病病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才慢慢改善。我的老师和师兄们,是第一批投入这种被不人道对待的精神病患者者的救世中,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治疗改得现代化。年我进入精神科工作,那时的台湾鼓励精神科医师去开疗养院,但几年就饱和了。我们比较幸运,开始从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性疾病、躁郁症等传统精神病人(或疯子),转向一般的抑郁、焦虑等神经症病人。治疗这些病人可以更加接近人性,这并不是说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等严重的精神病没有人性,而是他们好像旅行到另外一个更遥远的地方,我们一般人不容易到达他们那个世界。而对焦虑、抑郁和强迫等神经症病人,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去共情、了解甚至改变他们。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帮助这些病患,心理治疗自然就开始了。大陆和台湾省的心理治疗开始相当不同。大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心理学开放以后,慢慢地进来几路人马,有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人,也有李中莹和钟文鑫教授来这里授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德班。有了中德班以后,各国专业人员开始进入大陆。没多久,大陆经济起飞了,从一个资源不足的地方变成一个富裕的市场,各国专家更有动机来大陆讲课了。年以前,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三世界——欧洲跟美国之外——找了大概10个地方作为心理卫生试验地,包括菲律宾、中国台湾、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当时菲律宾政局不稳,联合国投入的资源很快就被破坏了,并没有累积下来。后来,因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我的老师林忠义、陈珠樟等几个教授,都到以哈佛为主的地方学习。20世纪50年代的哈佛以精神分析和社区精神医学为主,他们到哈佛学习精神动力心理治疗、社区精神医学和流行病学。在这批第一代老师的影响下,台湾精神医学界有了心理治疗的基础。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发明了精神病药物,哈佛这些地方不再以动力性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为主,而是被生物或药物精神医学所取代。以台湾临床心理学祖师爷柯永河教授为首的一批老师是第一波种子,也是政策的受惠者。他们回来以后自然而然地做心理动力学的教学,将相关专业知识传递给他们的弟子,维持一种信任、共享和提拔后进的状态,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钟文鑫教授到哈佛接受了完整的住院医师和心理治疗的训练,这是台湾心理治疗发展的高峰。但遗憾的是,钟文鑫教授回台湾不久就移民到了美国,台湾也因此断了一个传承。即便如此,心理治疗在台湾还是埋下了基础。在当时,药物精神医学是主流,大家迫切地想要帮助被手撩和脚撩拷起来的精神病患,所以心理治疗有一段时间被忽视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方面,因为认知行为治疗轻薄、短快的特点,几乎所有住院医师,以及心理系、咨商和临床心理系都以认知行为治疗为主,认知行为治疗开始被大量应用;另一方面,台湾社会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不同于大陆的街坊邻里,台湾的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是家庭,于是家庭治疗开始盛行。由此可见,精神医学或心理学以认知行为治疗为主,社工界是以家庭治疗为主。年,医院当精神科住院医师的时候,跟资深的社工师学习了家庭治疗,跟临床心理系的吴英章教授和李林英教授学习了认知行为治疗,跟陈珠樟教授和林倩教授学习了动力心理治疗。陈珠璋和林倩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到哈佛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以安娜·弗洛伊德为中心的自我心理学,也就是从弗洛伊德传承下来的经典心理学,即古典心理学。从20世纪60年代到我开始工作的80年代,期间有很多演化,导致这些知识没有被引进台湾。因此,我们这一代住院医师和心理师开始对心理治疗有了迫切的需要。随后,拉康的知识随着批判思潮被引进台湾地区,为了读拉康的文章,我自己虽然学习了一年半的法文,但是夹杂在语言学、哲学和精神分析之间,读起来还是非常吃力。而且拉康的理念离我的临床太遥远,所以没有多久我就放弃了。然后,我发现了客体关系理论。客体关系理论来自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被肯伯格等人引进美国,当时台湾的思想界流行拉康,所以知道客体关系的人非常少。于是,我们一边跟着陈珠樟教授做欧文·亚隆的动力团体治疗,一边自己慢慢摸索着学习客体关系理论。02 老师们获得一个学习的机会,是社会集体资源的受益者,他们将知识传递给我们会认为是理所当然。那时,我每个星期都接受XXX教授的1个小时督导。他一年陪我50多个礼拜,一共督导我多个小时,我从来没想过支付他一分钱,我唯一要履行的义务,就是把我跟来访者的对话写成手稿。我有一个朋友被大陆邀请来讲课,主办单位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一个小时元(台湾教师的学费是一个小时新台币元,人民币元),再加上住宿费和飞机票就可以了。那时工作坊一共有80多人,一人一天居然收0块左右,这让他很讶异。后来主办方解释说,收费太低,大家会不知道他的重要性,怕没人来听,他哑口无言。最后,虽然主办方给他一天块的酬劳,但他仍觉得相当困惑和愤怒,决定不再去大陆讲课,因为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待价而沽的有价位的商品。心理治疗在台湾一直都没有进入一种商品化或市场化的状态,虽然参加心理治疗工作坊也要付费,但那属于一种传统的师徒关系——你愿意投入我才愿意督导。台湾的治疗师很难理解大陆心理治疗的商品化,虽然台湾的心理治疗也收费,但收费的根本目的在于真正解决来访者的问题,而不是做专业训练。台湾的专业训练成本并不高,这些年也越来越上轨道。住院医师在训练里面至少要完成小时以上的治疗;心理师通常要完成三年到三年半的硕士学习、两年的理论学习和一年的实习,在一年的实习里,必须接待很多来访者。学校也会提供扎实的督导,看着学生一边做治疗一边修正。这样一年下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比较安全的空间做个案,例如学校的辅导中心;精神科医师有更多接个案的机会,医院也提供督导。在台湾,成为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师之后,对精神分析、团体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或家庭治疗的进一步训练需要付费。但并不是你付费就可以听课,还需要更多资格的考量,如果不能通过考量,就只能停在这里不能继续上升。你有没有能力解决来访者的困扰、来访者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你能否对他共情、你能不能理解来访者的需求,这些能力在心理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来访者觉得被理解并且也愿意理解你所描述的情况,他才愿意付出时间和金钱接受治疗,治疗才能得以展开。台湾的心理治疗师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anggoudasai.com/wgdsnr/9129.html
- 上一篇文章: 植物化学物质槲皮素可能对人类和动物的神经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